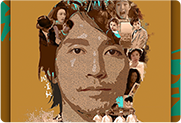对于广大的星迷来说,周星驰不再是一个艺人,不仅是一个演员,他是一个被异化了的演技之神的形象。
他成为这个时代华语电影人最成功的箭靶,被无数来自不同时空不同矢量的箭簇击中,他成为无穷观众倾销自己快乐、痛苦、忧伤、真诚和虚伪的对象,但大家却彼此有共鸣有误读,包括我在内,我相信观众不过是乌合之众,本来在消费主义时代无所适从,但还没有开始彷徨就找到了周星驰,尽管这些那些理解都是管中窥豹、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水中捞月,然而那似乎唾手可得的周星驰似乎就是为“我”而存在的,烫帖抚慰着在CPI指数日益远走高飞的小资、中产,坐临客回老家的农民工、正在建立人生观的大学生、耕田回屋休息的农夫,等等,大家都在各自的洞穴或者公开场合的电视机里,欣赏着周星驰的演员,但是周星驰却在改变。20年前,他当然不是如今的周星驰。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明星。鉴于粤语世界对于青年男子的褒扬性称呼,一个可能很有前途的靓仔,而已。
二三十年来,周星驰从一个寂寂无闻的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儿童节目主持人,到如今风靡国际的文化偶像,香港给予他的造化可谓不差,而他本人更是顺天应人、抓住机会适者生存,就好像水帘洞万千年来一直待在那里,却只有孙悟空跳跃过去,周星驰的进化过程,也绝对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不二模板。
周星驰电影的三个底线周星驰说他不懂什么后现代和解构之类,但也无妨他本人和他主演的电影成为一种拼贴。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使得观众和读者、尤其是好事之徒相信自己比作者更理解,一只母鸡下了蛋会咯咯的叫,宣布它的光荣,钱钟书说你觉得好吃,也不必去找它,事实上它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周星驰就是电影中的霸王,犹如歌坛里的许冠杰、讲坛上的易中天、演小品的赵本山、说相声的郭德纲,各位的舞台不同,行头不一,但是一旦出演,便各具特色的魔力,蛊惑人心,使人神魂颠倒,在一片激动和混沌之中, 以为有一大存在。周星驰和他的电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大体来讲,周星驰的进化历程有三变,从一个冲动的毛头小子幻化成惟我独尊的电影偶像。在《少林足球》的积极上进,以主旋律精神鼓舞香港人之后,周星驰向李小龙和动作电影致敬。《功夫》一出,豁然开朗,华语影坛为之一振。周星驰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回答自己怎样成为了一个文化英雄。而这个问题其实来历不明,回顾最近几年的评价之态势发展及激进过程,显然是媒体和专家、观众、网络共谋下的结论。周星驰也曾经给出过答案“自己去演,让别人去说吧”。然而这只是一个态度,我们还是难以判断他的至尊能力从何而来,他真的对从自己电影引申出去的亚文化无所知晓,全部的电影、电影的全部都只是电影而以为有一大存在。周星驰和他的电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大体来讲,周星驰的进化历程有三变,从一个冲动的毛头小子幻化成惟我独尊的电影偶像。在《少林足球》的积极上进,以主旋律精神鼓舞香港人之后,周星驰向李小龙和动作电影致敬。《功夫》一出,豁然开朗,华语影坛为之一振。周星驰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回答自己怎样成为了一个文化英雄。而这个问题其实来历不明,回顾最近几年的评价之态势发展及激进过程,显然是媒体和专家、观众、网络共谋下的结论。周星驰也曾经给出过答案——自己去演,让别人去说吧。然而这只是一个态度,我们还是难以判断他的至尊能力从何而来,他真的对从自己电影引申出去的亚文化无所知晓,全部的电影、电影的全部都只是电影而已,而没有自觉去渗入些微言大义?
《功夫》以打打杀杀为包装,小混混终于有机会成为大宗师,并不仅仅是个白日梦。周星驰想表达的,通过踊化为蝴蝶、夺命金针旋转成莲花已然说出,大宗师一定要超越胜负的蛊惑,方能进入是大存在的境界。周在最后大决战时摆出他心目中伟大的、永远浩气长存的李小龙的形象就说明了一切。《功夫》的魅力,首要在于内外兼修,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杂揉了众多经典元素和集体记忆。这次搞笑的语言和恶俗的搞怪主要由其他角色负担,夸张的对比、放肆的行为、无限的创意、热情奔放的豪迈都为故事的主题服务。总体而言,朴实与浪漫同在,粗俗共圣洁齐舞,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这更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世界。单论电影 中的功夫,就像沉积岩一样,层层迭迭地记录了功夫电影的发展史。
现在和未来的周星驰一定是华语电影向好莱坞宣战的代表,周星驰有自己的大绝招。在电影高度产业化的时期,是好莱坞速食面的时代,周星驰没有被同化,他的电影依然故我,周星驰的电影始终坚持三个底线,坚决执行一定不会踩过,那就是爱国主义(不会做汉奸)、家庭至上(浪子终究回头)、良心打底(无论感官和趣味如何刺激观众),并且强化了导演风格。《功夫》里的不得志的小混混始终做不成什么,周星驰大有向自我致敬的意味。而在即使得道之后,依然可以用踩敌人脚趾的方式去打败他们,充分说明了周星驰的童趣依然拥有,在这一刻,周星驰充分暴露了深刻与调皮同在的生活方式。他如今的生活就是拍电影,在这种生活里他的控制力是最强的、能力发挥也是最自如的。周星驰三变在《喜剧之王》追问演员的生存之道之后,周星驰结束了自从《赌圣》以来的巨星阶段。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再到《长江七号》,都是周星驰独角戏的演出。这无关戏份多少,一切以他的意志为核心价值,周星驰的气场俨然划一。《赌圣》之前,周星驰渴望做一个演员,但只能受老板和导演包括其他明星摆布。如今,周星驰摆布他电影中的所有元素,对于观众最大的欣慰就是尽管周星驰的产量很少,但质地优秀,值得期待。风格:从不由自 主的剧情片小子、到无厘头的小丑/英雄混一、再到作者电影的独一无二的主人公,自从被李修贤提携进入电影圈的最初,周星驰在《霹雳先锋》和《捕风汉子》中还是传统演员,基本按照剧本的要求来做文章。相对而言,在无线的电视剧《盖世豪侠》、《他来自江湖》,与李力持、吴孟达、万梓良的合作中,周星驰有意识的与李力持加入一些无厘头成分,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乱搞”和“神经病”,不过乱搞永远有一部分市场,观众开始模仿他的一些台词和动作,比如“坐下来,饮杯茶,吃个包”之类。其实在周星驰之前,无厘头最击中出彩的电影是姜大卫导演并主演的电影《猫头鹰》,他把此前自己兄弟主演的一系列邵氏动作片和流行的影视元素加以倒置、反讽和揶揄,但因为那个时代的观众还不懂得欣赏,未被观众接受。从《霹雳先锋》到《江湖上最后一个大佬》等电影,周星驰不过是不由自主的剧情片“小子”,作为小弟必须牺牲,作为儿子必须孝顺,作为雅皮可以胡闹,但总体上没有太多发挥。这个时期,他要感谢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流氓差婆》的导演刘镇伟,一个是《赌神》的导演王晶。
刘镇伟认出了周星驰的潜能,而王晶开创了赌博电影的戏路,再加上当年特异功能的流行话题,刘镇伟于是把多重元素打包,最终促成小成本电影《赌圣》创造香港电影票房记录。从《赌圣》开始直到周星驰客串王晶的《行运一条龙》,周星驰都是小丑/英雄混一的形象,这是一种将西方流浪汉小说、中国评书传统等结合起来的新型人物,周星驰以其难以说清帅还是丑的面目出现,总之是一定贱到极点也放浪到无限,丝毫不介意丑化各种身份和历史人物,小丑是清醒的,远远比英雄更自觉,关键就在于周星驰是自觉的无厘头。在这个期间的周星驰为金钱、美色、权利、地位而努力,归根结底是为无约束的自由,他可以伤害权贵但不伤害妇孺,他掠夺强势也不欺压弱势(在《审死官》和《白面包青天之九品芝麻官》当中,迅速做出反弹),《审死官》对于官和官场做出了终极消解,而《鹿鼎记》则对政治和皇权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阶段的周星驰和他的电影游戏感强烈,而最能代表的作品便是《大话西游》,将吴承恩的经典小说《西游记》进行再进一步的拆解,事实上吴承恩对于玄奘故事已经做出超级颠覆性的重构。一个山贼至尊宝最终成长为拯救者,其中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但从小丑变成了英雄。《国产凌凌漆》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挡周星驰从貌似英雄状成为小丑之后,不但任务完成而且抱得美人归。与之形成强烈影像的是《大内密探零零发》,无论周星驰怎样折腾,也因为其浮夸的风格而得不到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周星驰在《大话西游》和《食神》等未获奖项或票房肯定之后,在1997年回归之时推出了《算死草》,更是感官宣泄的高潮,妙就妙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上,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法庭上的三番争斗,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但是得来真是费功夫,否则冠冕堂皇之下,亲情可以湮灭、正义可以抛弃。到千禧年之际,周星驰推出反思作品《喜剧之王》,这是一次安身立命的长考。周星驰通过了考试,进化为独一无二的主人公。
《少林足球》是新后97时代最呐喊的一部电影,周星驰成为新英雄,顺利度过后97的关隘。借助于足球和功夫两大流行、时尚要素,再辅助于漫画精神和电脑特技,周星驰打造新时代的凯歌,超越自我,一群在金融危机煎熬中、失去往昔光荣的师兄弟,终于找到各自存在的位置,从此无厘头不再是最具有标签意义的词汇。《功夫》和《少林足球》一样,是从草根之中发掘神的力量和担当,再到《长江七号》则直接出现外星人,外星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人类心目中的“神祗”,能够抵达地球这个孤独的星球,他们便拥有超出地球人的能力。可以想象,周星驰和他的儿子是沟通孤独与温暖的桥梁。表演:从朴素无华的艺人、到光彩夺目的巨星、再到去掉一切外衣的演员周星驰因为《霹雳先锋》而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才得到无线电视台的看重,然而在电影领域却只是延续小子和平凡人形象,诸如《最佳女婿》中的无聊、《龙凤茶楼》的一般、《龙在天涯》的俗套等,周星驰只是充当导演的道具,根本无曾实现他的梦想。
《赌圣》的非常卖座改变了这一切,周星驰拥有了对片场的或多或少的控制力,王晶和李力持释放了他的潜能,给了他充分的表演空间,允许他参与电影的全过程,周星驰于是成为周星驰。这个时期的周星驰原创作品其实没有想象的多,绝大多数是对传统民间故事、经典电影的重拍、好莱坞电影的本地化,但是周星驰基本上将观众心目中的老故事、旧形象一扫而空,这一轮高速度的洗牌,周星驰和王晶、陈嘉上、李力持、黄百鸣、杜琪峰等人的成功合作,完全打乱了原来由周润发、成龙、李连杰等统治的市场,带领喜剧电影冲进动作电影的舞台,直至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合流,动作喜剧正式、最终成为香港电影过火、癫狂的新名片。周星驰这个时代,是票房号召力最强的巨星,他汪洋恣肆的诠释着一系列的经典,唐伯虎、武状元、特工、食神、韦小宝、赌侠、民族英雄等等,全部披上周星驰的外衣,不学无术、贪生怕死、怪力乱神、好吃懒惰、两面三刀等等劣根性逐一赠送给那些正统人物,却假借这些再创作的形象,更带出一个充满人性、真诚到无耻的“星爷”,观众由此得到全面的情绪释放,也将周星驰推上巨星的宝座,坐上香港电影第一座交椅,这个结果并不吊诡。周星驰将所有的角色都打回原形,不用脱掉衣服,大家都是一个模样,没有谁天然就比别人在道德上高出一筹,即便最后成为内心平静的人,也要经历历练的过程。
周星驰在《喜剧之王》的开头,面对大海高喊“努力”、“奋斗”,然后在电影中说出“我是一个演员”,分明是强烈感触到自己作为巨星的压力,也喟叹从小人物走到这一步的不易,尤其是从演员训练班到有机会做电影的主宰,第一步的难处和苦痛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少林足球》、《功夫》以及即将上映的《长江七号》,周星驰的表演风格是返璞归真的,他不再以夸饰的表情、舒展的肢体、喧嚣的台词和笑声来出现,而是外行潦倒、三餐不继、居无定所的垃圾佬、小混混、民工之类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周星驰向来被学院派或者正统批评者认为没有演技,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肯定,直到《少林足球》,周星驰放下原来的表演惯性,反而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承认,摧枯拉朽的连下七城。这是迟到的肯定,更是一种虔诚的道歉,周星驰对于香港和香港电影的热爱以及其高度专业精神,远远超出绝大多数评委的成见。如今的周星驰以无招胜有招,抖擞精神,以其宣扬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精神保障,无多余的表演才是最好的表演。台词: 从平凡俗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再到归于平淡。
周星驰在《赌圣》之前,并无多少话语权,最多也就是一些在电视台工作时的冷笑话和脑筋急转弯,问问大傻成奎安,一准是预料中的胜利。《赌圣》之后,周星驰确定了自己的模板式台词风格,密度非常大、语速极快、讽刺挖苦诙谐嘲弄他人为主、伴随高亢的坏笑,真的是荡气回肠,直达世间的秘密真相,在《鹿鼎记》中和师傅陈近南讨论起义的实质目的,不过是金钱、权力和女人,道出了许多观众懵懂之中的疑问。至于周星驰电影中的屎尿屁成分,则是其移植现实的案例,虽然对于很多人群尤其是女性有不尊重,但由于香港有比较成熟的电影分级,这些台词有一定的免疫力。周星驰在《白面包青天之九品芝麻官》和《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台词能力,很是绝妙。前者产生的语言暴力,甚至达到呼风唤雨的地步,将死人说活、直物弯曲,自然可以清正严明的驯服和惩戒一切非法大员。而后者则将风流才子唐伯虎赋予文武全才,无论是对对子、签卖身契还是终极对决杀父仇人,唐伯虎都能够以挥洒自如轻描淡写从容应对,而且更附加赠送了许多庸俗的言行,唐伯虎也是“人”啊,不过他是全才啊,但因为她的情趣与世俗人一般无二,观众很是欣慰。到了《少林足球》和《功夫》,周星驰放弃了成段的大排量台词,不过依旧坚持诙谐和自嘲。
综上所述,周星驰从弱势到强势,经历了一个牛市上扬的超级K线图,从随波逐流到睥睨古今、再到玩转时代。从题材上讲,由跟风到引流潮流、再到独树一帜。《赌圣》之前的周星驰,身不由己的接受安排,多数是跟风之作,没有多大特色,《霹雳先锋》是李修贤万能公司流水线作业的警匪片、《最佳女婿》是沟女喜剧、《情圣》则是楚原重复自我的偷盗电影等等。在《喜剧之王》之前,周星驰做了多年的票房冠军,《赌圣》、《逃学威龙》、《审死官》等等,引流赌片、校园卧底、古装讼片等亚类型的流行,到《少林足球》之类,再无人有能力复制和翻版,周星驰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周星驰的电影美学:狂欢化
从周星驰电影中配角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初级阶段时老一代明星到同时代艺人、再到独辟蹊径选择。最初于周星驰配戏的演员,多是前辈为主,最明显的就是李修贤、万梓良以及为张彻入电影行40周年的致敬电影《龙蛇争霸》,姜大卫、午马、陈观泰等出演,周星驰是少见的后来人。在其他电影中,萧芳芳、梁家仁、钟镇涛、李连杰等人也早已经成名。《赌圣》一举捅破天之后,周星驰多与吴孟达、张敏、邱淑贞、莫文蔚等人合作,多数都是同时期出道或成名的演员,在此期间周星驰启用了大量的奇形怪状的小配角,诸如八两金、如花、苑琼丹等。从《喜剧之王》开始,周星驰打造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底,比如田启文、陈国坤、冯勉恒等,或者发掘老前辈,比如梁小龙、元秋、张雨绮等,出手毒辣令人无法想象。在中后期周星驰电影中,所有角色都是为他服务,他渴望成为当然的核心,观众的情绪要为他而起伏变化。
周星驰似乎有一种科学拜物狂和广场情结,他的电影中的场景和人情,制造一种乌托邦,宣泄或者替代观众不可能实现的一些梦想,电影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制造梦幻。周星驰和刘镇伟、王晶、李力持等导演的合作,直接制造了灾难式的狂欢、奇观般的梦境,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说:“这种思维活动企图同时进行分析和综合两种活动,沿着一个或两个方向达到直至达到最远的限度,而同时仍能在两极之间进行调解。”《赌圣》、《赌侠》、《鹿鼎记》、《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国产凌凌漆》、《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等电影都是如此,一方面彻底消除各种角色的神圣光环,继而将其姿势绝对的放低,所谓偶像、英雄、清官、好汉、高手除了有一点点良心做底牌之外,不过是随波逐流之徒甚至不择手段,话语权掌握在周星驰和导演的手里,他们肆无忌惮的将传统的正典叙事、经典人物还原,大家斗不过人性,没有那么多圣人,告子说的食色性也,儒家克己复礼几千年也不过是功亏一篑。作为观众,我们能够接受的事物,总是与我们内心某种期望有关。
《大话西游》后,周星驰电影被回溯性地指认为是后现代人的精神乳汁,他本人也坦然认可这种解读,并加以主动性哺乳。进入新千年后,周星驰只拍摄了三部电影。《少林足球》以一种草莽的自信取得香港影史最高票房记录,《功夫》的精神跳板无疑是李小龙和功夫,《长江七号》是家庭、外星人和农民工。在我看来,这三部电影最重要的特点是依旧保持了周星驰一贯的电影美学:狂欢化。小丑和英雄集于一身的先行性设计,是周星驰最有力的美学武器,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视野。《喜剧之王》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普通叙事的电影,从此以后周星驰成为概念的主人和奴隶,他一定要先寻找好可以附着的概念,才能展开他的内容。狂欢化使热情奔放创意无限成为可能,周星驰往往会选择狂欢节上小丑的角色来搬演,山贼至尊宝如此,宋世杰/包龙星如此,《少林足球》和《功夫》里的两版阿星依然如此。狂欢化的小丑,最高原则是笑,包容一切荒诞和离奇,否定一切神圣和理性,一根筋似的往前冲,泡妞、敛财、刻薄、追求、憧憬,都在这笑中实现,笑与被笑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小丑最终会变成英雄。周星驰从1980年代末期无数的电影人中,走到今天的地位,可以庄严,可以狂欢,本身便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传奇。
要狂欢,就需要一个舞台。至尊宝有一个上下五百年肆意转换的月光宝盒,邪典状师有衙门大堂,《少林足球》是足球场,《功夫》则是猪笼城寨,这些舞台使现实、历史、经典退后成为飘渺的背景,周星驰自如地鼓捣自己的世界,颠覆、夸饰、戏仿、反讽,荒唐之余,有一种粗砺的真诚,我就是自己,我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去他妈的教条与传统。狂欢首先要坐低,甚至于趴在地上。小丑并不负担世俗社会对英雄的寄予,然而周星驰总能够通过转化/置换出英雄来,这只能说明周星驰内心深处依然有一种深邃的英雄情结。小人物最后的升华/加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周星驰对自己的要求,但是从美学上讲丧失了狂欢节本应有的落寞。周星驰至今尚没有一部电影做到小丑最后还是小丑,从没有来到哪里去,一切过程都如同一场梦一样,《大话西游》曾经无限可能地接近了这一目标,然而前两部票房的受挫使得第三部遥遥有期到2005年的《情癫大圣》,但是再也不会是当年的那个故事和情怀。
周星驰和狂欢节结合的另外两大特点,就是言辞粗俗和女性地位的缺失。粗鄙的谩骂、无耻的诋毁、动辄就提下半身器官和排泄物,随意问候他人母亲,民间语言是周星驰电影语言里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九十年代初期的周星驰电影是民间语言在银幕上疯狂滋生的时代,充分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并且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语文。
周星驰依旧在进化中,期待新的突破
刻薄一点讲,这是一个大师死掉的电影年代,宽容一些讲,现在的电影缺少大师,全世界都如此,不唯独中国例外。如今,老百姓的娱乐方式极为丰富,电影只是其中一个选择的前提下。再感叹艺术电影难做,其实就是矫情,2007年内地生产了400部电影,请问有几部电影敢宣称自己是成功的艺术电影,同样的缺憾是也没有几部可以说是成功的商业电影。在如今的年代,商业电影其实比艺术电影更加困难。从美国《首映》和《帝国》及法国《电影手册》等杂志排的艺术大师和独立导演的TOP榜可以看出,大师们都逐渐年华老去,现在早已经是商业电影的天下。就连已然被尊称为大师的王家卫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也撒脚丫子在商业电影的路上,众多第六代导演浮出水面,这是一个进步,只有商业才能面对更多的老百姓,更重要的电影从本质上讲是商业产品。在《大话西游》前,评论界忽视周星驰和其他商业电影存在的价值,如今影评人认同周星驰等人的电影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周星驰的电影在商业之外,更有人生况味在。周星驰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码,而在这个序列中,《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到《功夫》成为一个新的谱系。《喜剧之王》是对周星驰个人和演艺圈行业的总结性陈词,《少林足球》鼓舞社会和个人奋斗,而《功夫》则是以全体中国人为奉献的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功夫,这便是我们中国人可以想到的、做到的。和周星驰比较,华语电影的投资人和资金不可谓不多,但是电影质素的普遍低层次复制,动辄以艺术/卡司/观众口味/个人表达为借口,只能说某些电影人诚意不足。
周星驰说自己不再和别人比较成败,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有意为之。周星驰在《功夫》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一个在十年前荒诞的命题,就是怎样理解自己在内地被某些学术界人士称为后现代主义解构大师(那一秒,我看到了他的神情),他的回答也很是有趣——自己去演,让别人去说吧,周的态度从电影里可以被清晰地看出,一个棒棒糖连接了童年的拔刀相助和作为不得志的小混混,通过哑女黄圣依他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人。而在即使涅磐之后,仍然用踩敌人脚趾的方式去打败他们,则说明了周星驰的童趣依然拥有。周星驰曾经说过,做人没有理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但周星驰也有自己的缺陷,虽然他可以使用好莱坞或其他财阀资金,但他的电影和故事内容很难脱离香港语境,特本人有时候很难避免厌女症和躁动狂,无论他如何谈恋爱,在电影上总是将女人作为他实现某种目的的精神投射,张敏、黄圣依、张雨绮都是这一类型,她们无一不是美貌和智慧并重,但周星驰的欲望表现却是将她们神圣化,赵薇、莫文蔚都是来解决问题的,拯救周星驰于危难之际。在周星驰电影中,女性多数是作为看/被看/拯救/被拯救的形象出现的,或者是精神的中间件,使周星驰本人获得心灵上的救赎。
诚然周星驰在电影上从来就不玩弄女性,但是女性并没有什么实质地位,只是周星驰色欲/精神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朱茵、张敏、赵薇、黄圣依和如花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便是狂欢节的副作用。(写于《长江七号》公映之前;特别感谢老家日照的亲朋潘培金、潘宁、蚂蚁等人对我的支持、宽容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