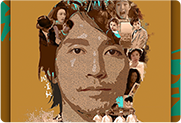都说真实的星爷内向低调,和他的银幕形象反差到近乎分裂。但现在我们相信这并不准确。逻辑很简单:一个从影20年来始终在以其商标式的癫狂跳脱示人的人,不可能缺少鬼马的基因。正如戏里戏外,成龙永远是那个大咧咧的大哥,而张曼玉则总笼罩着一层疏离而敏感的气质。我们从最早的TVB儿童节目《430穿梭机》到随后剧情各异水平参差的50部影片里,一直可以看到那个永在天马行空搞怪耍宝的演员。这个演员始终是票房数据和观众笑声的最大保证,而他的成功,显然需要感谢天赋。
这种天赋就是我们叫作“无厘头”的本领。无厘头平民、粗鄙、夸张、直接,远离精致风雅的文人趣味,也拒绝淳朴天真(尽管也会不乏狡猾)的乡土风尚,是一种彻底草根的市井文化,因此发扬光大于最具市井气息的香港几乎成为必然。而相貌体格庸常,成长于底层九龙小市民家庭、又没有接受过较高文化培养的周星驰,自然而然又忙打误撞地成了最适合的无厘头诠释者。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一个明星——星仔——横空出世。
如同动作喜剧之于巴斯特"基顿,莎士比亚经典之于劳伦斯"奥利弗,无厘头正是周星驰呼吸一般的才能。仅仅由短期速成的艺员训练班出身的他,表演自然不属于学院派,尽管他承认自己看不懂《一个演员的修养》,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下的方法派演技大师,本色演出是他安身立命的法宝。他能活灵活现地演绎街头混混的猥琐、小市民的短视、小人得志的跋扈、脓包蛋的窝囊劲、狂狷之徒的放浪,用漫画式的夸张表情、夸张动作和夸张声音塑造了一个个信口开河,没老没少,狐假虎威,油头滑脑的角色。在周星驰电影里,低俗不堪又奇思妙想的爆笑包袱总以超群的速度密集袭来,颠覆经典嘲笑传统的情节线索虽然散漫但自成系统,比肩漫画人物的角色设定更是夸张到令人难忘。周星驰没有卓别林式的招牌行头,也没有吉姆"凯瑞式的橡皮脸,但他平庸的相貌和幅度不大的肢体演出就是让张口大笑、倒吸一口凉气和提肩后退这三个周氏动作变成了华语地区几乎整整一代人狂喜的原因和效仿的对象。
香港无厘头电影并非周星驰的专利,癫狂喜剧在七十年代许氏兄弟作品中已近成型,而和周星驰同时代的影人如刘镇伟、李力持等,也俱是个中翘楚,甚至不妨称之为周星驰喜剧的真正奠基人。然而最终我们把无厘头之王的头衔赠予周星驰,正因为他契合无厘头真髓的个人气质才能把这一市侩艺术发挥到极致,并且二十年来,只有他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一直坚持。
但二十年过去,53岁的发哥还是发哥,47岁的华仔依然是华仔,而45岁的周星驰已经从“星仔”变成了“星爷”。称呼的变化,并非因为年齿的增长,而是传递了两重意义:周星驰喜剧获得巨大成功的明证和周星驰本人心态的转变。除开惊人的表演天赋,这两者的凸现又都缘于他气质中的另一大构成:矛盾。
周星驰的里里外外充斥了大量矛盾。从他出道至今,对其评价就始终处于两极,誉之者可以将其拔高为“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毁之者则斥其为龌龊下作的低俗文化象征;他在电影里是飞扬跋扈浅薄唐突的得志小人,而在公众面前,他却是木讷寡言高深莫测的大人物;他以语言类表演为特色,然而出了粤语区,在内地和台湾这两个华语文化母体却只能依靠配音演员石斑鱼的声线发挥;他在向世人大声宣告自己“其实是一个演员”之后,却转身变成了一个导演。
他的作品也充满矛盾,他本人并不重视且票房失利的《大话西游》在内地成了“周星驰热”的永恒发动机;他在自己最具自传色彩且内涵最为严肃而丰富的作品(《喜剧之王》)中却设计了一个最莫名最胡闹的结局。在剧情安排上,周星驰电影最擅长的也是放大矛盾和反差:在“赌圣”系列里,他是天赋异禀的奇才,然而又是猥琐粗鄙的混混;在《破坏之王》里,他是老实巴交任人宰割的餐厅小伙计,却能击败不可一世的功夫高手;在《回魂夜》里,他是无所畏惧的捉鬼大师,但又是精神病院里丧失理智的疯子。归结起来,周星驰扮演的角色原型不外乎两种:一是一无所长的卑微小人物,二是身怀绝技的人中豪杰,然而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两种原型始终在衔接互换和彼此融和,进而制造出无穷多的亚型:先卑微后超人——包龙星(《九品芝麻官》)、何金银(《破坏之王》)、阿星(《功夫》);先超人后卑微——宋世杰(《审死官》)、史蒂芬·周(《食神》);“伪装”卑微的超人——唐伯虎(《唐伯虎点秋香》)、周星星(《逃学威龙》系列);既卑微又超人——凌凌漆(《国产凌凌漆》)、大力金刚腿(《少林足球》)。
但无论如何,周星驰所有的角色最后都会变成或本领盖世或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但又都必须贴上足够多的“草根”标签。无论是韦小宝(《鹿鼎记》)孙悟空(《大话西游》)这样由草根自下而上变化式,还是苏灿(《武状元苏乞儿》)李泽星(《百变星君》)这样由上而下变回草根式,周星驰人物必然会呈现出典型的市井小人物特征:虚荣、敷衍、粗俗、急智,然而其言其行尽管不乏颠覆疯狂,但最终仍会遵守传统是非正义的价值观——这其中包藏了一组组大大小小的矛盾及冲突。
心态及身份的转变更是矛盾冲突的结果:周星驰毋庸置疑是一个天才的创作型演员,但随着不断成功带来的压力又令他对影片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逐渐他发现没有导演能够达到他的标准,于是他做了自己的导演。在面对记者时,他坦承自己做导演有“甚至说都说不出来”的辛苦,很乐意做回“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演员,然而马上又认同自己更愿意“做导演”的看法;在创作上,他始终在求新求变,不做“太多人做过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孙悟空的恋爱史、武功盖世的唐伯虎、大内密探搞科技发明、少林和尚踢足球、CG特效耍功夫这些奇思妙想又滑稽热闹的故事,而(华语电影)从来没人做过的“科幻的”“家庭的”《长江七号》又成了他的新选择。但他又表示,自己一定要坚持做草根题材,不会没有“自知之明”去不“量力而为”地拍非喜剧的战争片历史片;在效率上,他说他很乐意像以往那样一年拍好几部电影,《功夫》和《长江七号》的漫长制作周期只是“意外”——我们丝毫不怀疑他如此表示时的真诚,但我们也知道他对影片精益求精的苛刻态度决定了未来的周星驰电影依然将会是数年才有一部的低产制品;他是香港电影的骄傲,然而他本人又和向来团结的香港影人集体渐行渐远,而吴孟达、李力持、罗家英等故旧们的“众叛亲离”更非八卦记者臆造。另一方面,1999年以来他的三部作品讲的都是大陆故事,但三部影片的核心成员和工作方式依然坚持纯港风味;他既不像成龙刘德华那样频频参与“两会”、投身内地社会活动、接拍商业广告来令自己纳入内地体系,也不像杜琪峰那样固守香江拒绝北上。
在摄影棚里,他是颐指气使事必躬亲的暴君导演,但在电影以外的公众视线里,他却少言寡语期期艾艾——实际上,他面对媒体的落落寡欢和语焉不详,并非刻意为之的装傻充愣,也不是真的内向羞涩,他当然知道传媒宣传的重要和必要,但他又本能地厌倦这类姿态上正襟危坐而内容上不断重复的把戏;他是大众传播里永恒的宠儿,然而他本人又刻意回避私生活的曝光,迄今为止无论在报刊杂志还是在电视互联网上,几乎都找不到一次像样的周星驰访问:他从不像姜文那样挑衅记者,也不会像被激怒的萨科齐那样拂袖而去,更不会像多数公众人物那样八面玲珑见招拆招。他几乎不会“不配合”,更不会拒绝回答问题,但记者的努力和好奇心总会被他如打太极一般慢吞吞卸去力道,然后他自己再王顾左右而言他。从他的嘴里从来没有任何“爆料”,他会提供一些众所周知的信息,但常常最终又模棱两可。因为他始终觉得观众喜欢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即可,他说,“我相信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的为人,一来大家不清楚;二来就算大家知道一点,也未必是真的;第三,根本上没有人有太大的兴趣。”
星爷如是说。
面对我们送上的“史匹堡和楚浮合体”的高帽子,星爷一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认不出特吕弗的照片,经过我们提醒这是《四百击》的法国导演时,他才恍然大悟地反应过来,“把我和大师放在一起说?”“我也是大师了?”“谢谢你啊。”然后记者问:“我们现在都说你是大师了,你会怎么想?”他笑了:“请你吃饭啦。”实际上,在2007年圣诞节的前三天,星爷走马灯一样四处做宣传,记者一路跟随,纪录下了星爷的各种言论。
周:以后的电影后期制作能不能进度快点啊?
特效师:我们拍的是科幻片!
周:那以后能不能去掉那些科幻元素啊?
特效师:拜托,我们特效师要吃饭啊!
——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和剧组成员临演相声
我自己的演技也不是特别好。
——谈自己没信心演内地民工。
只有飞碟是扁的好不好?
——面对电视主持人质疑他是否真的目击过UFO。
你看我姐姐像不像李小龙?
——在看童年时的家庭照片时。
所以要找一个天才喽。
——当记者问到徐娇没有表演经验时怎么办。
就是现在不无厘头了,你说新不新?
——谈及有什么“无厘头”创新。
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信心。
——谈及针对《投名状》和《集结号》的高票房,自己的心态。
电影还是要新鲜最重要,可能有电影人觉得很多人做,我也做——很多人做就代表很成功嘛,市场有保证,风险就小。但我是不一样的看法。
——阐述自己选材的标准。
从历史上看,家庭电影都是最卖钱的。史匹堡的电影都是家庭电影。
——谈到《长江七号》是一部什么类型的电影。
我的电影当然有喜剧,但是也会有别的元素。
——说到自己的电影为什么“没有那么搞笑了”。
在我以往的经验来说,失败是很重要的。
——坦承成功积累的压力更难受。
电影人的工作就是猜观众喜不喜欢。
——研讨电影题材时的主要任务。
电影人选择了正确的题材,但他做得不好;有的时候做得很好,但选材选得不对,效果都不会好。电影就是那么复杂。
——其实很简单地剖析了电影创作的规律。
中国电影刚开始嘛,你要给它时间。
——说到中国电影开始有类型片倾向。
可能我拍电影的时间也不会很多,所以不会浪费时间拍那些不好的,我要尽我自己的努力做一些好的。
——回答几乎惟一一次令自己情绪激动的问题:“是否会因为高报酬而接手自己不看好的题材”。
原文作者:唐味歧